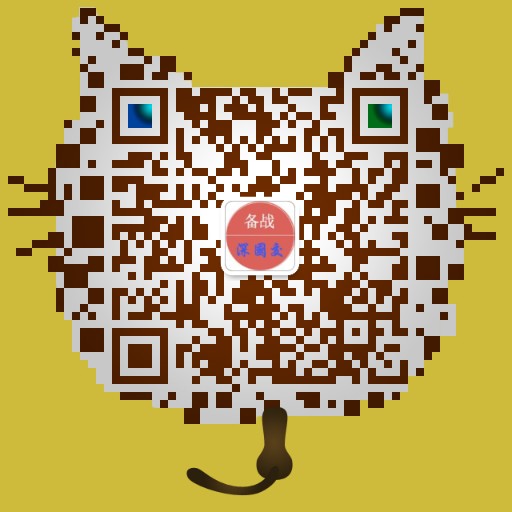当前位置:首页 » 深国交哲学社 » 正文
-

在当前国内关于俄乌战争的讨论中,有很多关于“战争是否正义”、“战争中是否有正义”、“国际关系是否仅是利益的结果”的讨论。有的人拥护普京的决定甚至认为地缘政治中没有道德,或者是强权即正义;有的人反对并且主张自己是“反战人士”。这种相反的立场都无可非议,但重要的是参与公共讨论的各方如何论证自己的观点。 但是,无论是在微博、微信还是在豆瓣,都充斥着大量的“独断论”。他们用自己偶然间看到的一个表面上有道理的论断、或者是自己在基础教育中被教导的观念进行论战,对正义问题进行“宣判”,并对不同的观点嗤之以鼻。但如果问他们为何支持这个观点,他们大概会诉诸一些假想情况、人身攻击,唯独无法理性地为自己的观点辩护。 其实在没有经过充分的、理性的公共讨论之前,没有人能宣称自己掌握着真理。 我翻译这篇文章的目的是试图将理性的力量引入当前的公共思考之中。哲学可能带不来什么洞见,但是可以让我们在思考某个问题的时候更加条理和理性。如果对于道德的思考能唤醒读者的良知,就更加如我所愿了。 最后,十分感谢原文作者Seth Lazar教授的授权和支持。Lazar教授的支持让我倍受鼓舞。 (续上文)  战时正义(Jus in Bello)
战时正义(Jus in Bello) Walzer和对他的批评
Walzer和对他的批评体现在国际法中的传统主义战时正义(jus in bello)认为,战争中的行为必须满足三个原则: 1. 区别原则。以非战斗人员为目标是不允许的[14]。
2. 合比例性。只有在伤害与攻击所要实现的目标合比例的情况下,才允许附带性地伤害非战斗人员(即在可预见的情况下伤害他们,但不是故意的)。
3. 必要性。只有在追求自己的军事目标时,选择的是伤害最小的可行手段,才允许对非战斗人员进行附带性伤害。 这些原则将战争的可能受害者分为两类: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这些原则没有设置对于杀害战斗人员的任何限制。但是,除了 "最高紧急状态",即为了避免不可接受的威胁而必须故意杀害非战斗人员的罕见情况外,非战斗人员只能在非故意的情况下被杀害,即使如此,也只有在他们遭受的伤害是必要的并且与战争的预期目标合比例的情况下才可以。[18] 那么,如何判断是否为战斗人员就变得很重要。本条目采用了一个保守的定义。战斗人员是指处于战争状态的的有组织武装部队的(大部分)成员,以及直接参与敌对行动或具有持续战斗功能的其他人(讨论见Haque 2017)。非战斗人员不是战斗人员。当然,也有很多疑难情形,特别是在不对称战争中,但这里不考虑这些。"士兵"(Soldier)可与 "战斗人员"(combatant)互换使用,"平民"(civilian)可与 "非战斗人员"(noncombatant)互换使用。 传统的正义战争理论和国际法都明确允许按照这些限制条件进行战斗,而不考虑其目标。换句话说,他们赞同: 战斗人员平等性(Combatant Equality):满足区别原则、合比例性和必要性的士兵被允许进行战斗,无论他们为什么而战。[19] 我们在下面讨论合比例性和必要性;现在让我们集中讨论Michael Walzer关于“区别原则”和“战斗人员平等”的有影响力的论证,它已被证明是非常有争议的。 每个人都享有生命和自由的基本权利,这些权利禁止他人以某些方式伤害他们。由于战争显然涉及剥夺他人的生命和自由,Walzer认为,只有当每个受害者 "通过自己的某种行为......交出或失去了自己的权利",战争才是可允许的(Walzer 2006:135)。然后,他声称,"仅仅通过战斗",所有战斗人员 "就失去了他们的生命和自由的所有权"(Walzer 2006: 136)。首先,仅仅通过对我构成威胁,一个人就和我划清界限了,背离了我们共同的人性,因此他自己就成为了致命武力的合法目标(Walzer 2006: 142)。其次,通过参加武装部队,战斗人员 "允许自己被塑造成一个危险的人"(Walzer 2006: 145),从而交出了自己的权利。相比之下,非战斗人员是 "拥有权利的人,......他们不能被用于某种军事目的,即使是合法目的"(Walzer 2006: 137)。这就在辩论中引入了可杀性(liability)的概念,我们需要仔细定义这个概念。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人具有可杀性,意味着对她的杀害并非错的。通常情况下,就像Walzer那样,这被理解为权利:每个人一开始都有生命权,但这一权利可以被放弃或丧失,因此,一个人可以被杀死,而这一权利却没有被侵犯或违反。Walzer和他的批评者都认为,只有当一个人失去了对其生命权的保护,或者由此获得的好处确实非常大,足以使她虽然被错怪,但杀死她并不是毫无道理的,她的权利才是可以被允许侵犯的。Walzer和他的批评者认为,这种情况在战争中是非常罕见的,只有当不故意侵犯人们的生命权的下场是像纳粹在欧洲的胜利那样迫在眉睫的灾难时才会出现(纳粹的例子是一个最高紧急情况的例子)。 这些简单的论证阐明了区别原则和战斗人员平等——前者,因为非战斗人员保留了他们的权利,所以不是合法的攻击对象;后者,所有战斗人员都失去了他们的权利,不管他们为什么而战:因此,只要他们只攻击敌方战斗人员,他们的战斗就是合法的,因为他们没有侵犯任何人的权利。 这些论点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对“战斗人员平等”最简单的反对意见是它与“合比例性”相冲突(McMahan 1994;Rodin 2002;Hurka 2005)。只有在与所追求的军事目标合比例的情况下,才允许非战斗人员的非故意导致的死亡。这意味着该目标值得那么多无辜的痛苦。但是,军事目标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它们的价值取决于目的的价值有多大。对于青年党对摩加迪休(索马里首都)的占领,或者伊拉克在1991年科威特的领土和石油储备的占领来说,有多少无辜的人死亡才是与此合比例的?在两种情况下,答案都很明显:没有一个人。 合比例性是指权衡所造成的恶与所避免的恶(Lee 2012)。但不正义的战斗人员的军事胜利并不能避免邪恶,它本身就是邪恶。故意造成的邪恶只能增加,而不是抵销非故意的邪恶。因此,“战斗人员的平等”不可能是真的。 其他反对战斗人员平等的论点集中在Walzer对一个人如何失去生命权的描述上。他们通常从接受他的前提开始,即战争中可允许的杀戮并不侵犯受害者不被杀的权利,至少对于故意杀戮来说是如此。 [20] 这与以下观点形成对比:有时人们的生命权可以被剥夺,因此尽管侵犯了人们的权利,但战争还是可允许的。然后,Walzer的批评者表明,他关于我们如何失去生命权的说法是根本不靠谱的。仅仅对他人构成威胁——即使甚至是致命的威胁——并不足以证明一个人的基本权利就此丧失,因为有时一个人威胁他人的生命是出于非常好的理由(McMahan 1994)。库尔德佩什梅加的士兵为拯救雅兹迪人免遭伊斯兰国的种族灭绝而英勇作战,但他们并没有因此失去不被对手杀害的权利。在追求正义目标的过程中对他人造成威胁,而这些人正积极地试图阻挠这一正义目标,这不能使一个人不被这些人伤害的基本自然权利无效或失效。基于同意的论证作为“战斗人员平等”的一般辩护理由也同样不可信。如果非正义的战斗人员放弃了他们免受致命攻击的权利,而这样做又会使正义的战斗人员同样失去这项权利,那么非正义的战斗人员就会有所获益。而在大多数观点中,许多非正义的战斗人员没有什么损失,因为通过参与非正义的战争,他们即使没有失去这些权利,至少也削弱了。相比之下,正义的战斗人员则会有所损失,且不会有什么收获。那么,为什么为正义事业而战的战斗人员会同意被他们的追求不正义目的的对手伤害? Walzer主张“战斗人员平等”的理由在于表明正义的战斗人员失去了生命权。他的批评者已经表明,他为此目的的论证是失败的。因此,“战斗人员平等”是错误的。但他们所证明的还不止这些。在Walzer研究我们失去生命权的条件的启发下,他的批评者在理论上取得了进展,对战时正义(jus in bello)的其他核心原则提出质疑。他们认为,与Walzer相反,构成威胁并不足以产生可杀性(McMahan 1994年,2009年)。但他们也表明,自己构成威胁也不是可杀性的必要条件。这一点比较有争议,但修正主义者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在战争中和在其他地方一样,可杀性的基础是一个人对所造成的不法威胁的责任。例如,美国总统对她命令的无人机袭击负有责任,即使她没有亲自开火。 正如许多人指出的那样,这一论点破坏了“区别原则”(McMahan 1994;Arneson 2006;Fabre 2012;Frowe 2014)。在许多国家,非战斗人员在加强军事力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现代工业化国家,多达25%的人口在与战争有关的行业工作(Downes 2006: 157-8;另见Gross 2010: 159;Valentino et al. 2010: 351);我们为交战方提供关键的金融和其他服务;我们支持和供养作战的士兵;我们纳税,在民主国家我们投票。我们长期以来对国家能力的贡献使它有力量和支持来集中精力进行战争。[21]如果国家的战争是不公正的,那么许多非战斗人员要对所造成的邪恶的威胁负责。如果这足以让他们失去生命权,那么他们就是可允许的被攻击的目标。 McMahan (2011a)试图避免他的论证的这种令人不安的含义,他认为不公正一方的几乎所有非战斗人员(不公正的非战斗人员)都比所有不公正的战斗人员责任小。但这涉嫌双标,提高战斗人员的责任,而降低非战斗人员的责任,并且在他关于可杀性的论述中搞错了一个核心要素。在他看来,一个人之所以要对他在自卫或他卫中被杀负责,是因为在那些能够承受不可避免和不可分割的伤害的人中,他是对这种情况的发生负有最大责任的人(McMahan,2002年,2005b)。即使非战斗人员对其国家的非正义战争只负有最低限度的责任——也就是说,他们不应受到指责,他们只是自愿以可预见的方式促成了这一结果——在McMahan看来,这足以使他们具备可杀性,如果这样做是为了拯救完全无辜的战斗人员和正义一方的非战斗人员的生命的话(特别见McMahan,2009:225)。 一种回应是拒绝这种关于“对战争负的责任”如何决定“可杀性”的比较性说法,而主张采用非比较性的方法,根据这种方法,一个人的责任程度必须大到足以证立对他的基本权利进行如此严重的减损。但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肯定要承认,非正义一方的许多战斗人员对非正义的威胁没有足够的责任来使他们可以为自己被杀负责。无论是由于恐惧、厌恶、原则还是无能,其实有许多战斗人员在战争中完全没有作用,对其一方造成的威胁几乎没有任何贡献。被广泛引用的S.L.A.Marshall的研究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只有15%-25%的盟军士兵可以开火(Marshall 1978)。大多数士兵对杀戮有一种天然的厌恶,即使是密集的心理训练也可能无法克服(Grossman 1995)。许多人对不正义的威胁的贡献并不比非战斗人员大。他们也缺乏 "犯罪意图"(mens rea),而这种 "犯罪意图 "可能使他们在没有重要的因果关系的情况下具有可杀性。他们往往不应受到指责。剥夺他们的生命权并不是对他们的行为的适当回应。 如果Walzer是对的,在战争中,除了在最高的紧急情况之外,我们只可以故意杀那些具有可杀性的人,如果相当一部分不正义的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对不正义的威胁负有彼此相同的责任,如果自己的可杀性是由自己对威胁的责任决定的,那么我们必须在两个难以接受的选择中做出决定。如果我们为可杀性设定一个较高的门槛,以确保非战斗人员不具有可杀性,那么我们也将免除许多战斗人员的可杀性。 在不涉及最高紧急情况的普通战争中,故意杀害这种无责任的战斗人员是不允许的。这让我们走向了一种和平主义——虽然战争在原则上是合理的,但要在不故意杀害无可杀性者的情况下作战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在实践中我们必须是和平主义者(May 2015)。但如果我们把责任的门槛定得很低,确保所有非正义的战斗人员都要具有可杀性,那么许多非战斗人员也要具有可杀性,从而使他们成为被允许进攻的目标,这严重破坏了“区别原则”。我们在和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纠结,一边是和平主义,另一边是现实主义。这就是正义战争理论的 "责任困境"(responsibility dilemma)(Lazar 2010)。
 杀害战斗人员
杀害战斗人员只有当我们能够解释为什么在战争中杀死一些战斗人员是允许的,但我们并没有因此被允许杀死敌国的每一个人,正义战争理论才有意义。在这里,现实主义和和平主义的竞争是最有说服力的。因此,最近有如此多的工作集中在这一主题上,并不令人惊讶。我们不能在这里公正地对待所有的论点,而是要考虑三种回应:全面的修正主义者(all-outrevisionist);温和的传统主义者(moderate traditionalist);以及全面的传统主义者(all-out traditionalist)。 第一个阵营面临两个挑战:将故意杀害显然没有可杀性的非正义战斗人员正当化;但要做到这一点,又不能重新打开“战斗人员平等”的大门,或进一步破坏“区别原则”。他们的主要举措是主张说,尽管只是从表面上看,所有而且只有不公正的战斗人员实际上具有可杀性。
McMahan认为,可杀性事实上不需要预先假定对非正义威胁负有责任。相反,对于正义战斗人员合理地认为非正义战斗人员应当负责,非正义战斗人员对这一信念的责任就可能足以成为其丧失权利的理由(McMahan 2011a)。有些人认为,战斗人员对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的责任就足够了(将他们比作自愿的人肉盾牌)。[22] 更为激进的是,一些哲学家放弃了对个人责任的坚持,认为非正义战斗人员对促成非正义威胁负有集体责任,即使他们个人并没有发挥作用(甚至发挥了相反作用)(Kamm 2004;Bazargan 2013)。 Lazar (forthcoming-a)认为这些论证是没有说服力的。共犯可能与一个人在战争中需要承担的代价有关,但大多数自由主义者会对因其他人所做的事情而失去生命权的想法感到不快。如果战斗人员可以为其战友的行为承担共犯意义上的,那么为什么非战斗人员就不能承担共犯意义上的可杀性呢?
对其他人的错误信念的责任似乎确实与自卫和他卫的伦理有关。也就是说,考虑一个白痴假装成自杀式炸弹袭击者来恶作剧,并被警察射杀(Ferzan 2005; McMahan2005c)。杀死他在客观上是允许的吗?这似乎很值得怀疑。警察有理由相信这个恶作剧者构成了威胁,这显然减少了杀死他的不法性(Lazar 2015a)。当然,恶作剧者的过错也为警官免除了所有罪责。但杀死恶作剧者似乎仍然是客观上的错误。即使某人对错误信念的的责任可以使杀死他在客观上是可允许的,大多数哲学家都同意,许多不公正的战斗人员对他们的战争的不公正性并没有责任(McMahan 1994;Lazar 2010)。而对信念的无过错的责任可以使一个人成为可允许被杀害的目标,这就更不靠谱了。即使是这样,这也有利于温和的战斗人员平等,因为大多数正义的战斗人员也对非正义的战斗员的合理信念负有无过错的责任,即他们对自己的被杀负责。 温和的传统主义者认为,我们只有通过承认一种温和的“战斗人员平等”的形式,才能避免责任困境中的现实主义和和平主义之争。该论证分三步进行。首先,设定一个非比较性的、较高的可杀性门槛,这样在大多数冲突中的大多数非战斗人员都没有足够责任以至于具有可杀性。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战争中杀害平民是如此难以辩解。当然,这也意味着许多战斗人员也将是无辜的。那么,第二步就是捍卫道德区分(MoralDistinction)原则,根据这一原则,杀害平民比杀害士兵更糟糕。如果士兵有可杀性,而平民没有责任,这显然是正确的。但挑战在于,如何证明杀害无可杀性的平民比杀害无可杀性的士兵更糟糕。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即使故意杀害无可杀性士兵的是可允许的,也并不意味着故意杀害无可杀性的非战斗人员是可允许的。当然,人们仍然可能争辩说,即使道德区分是真的,我们也应该赞同和平主义。但是,这是第三步,某种行为的错误性越小,实施该行为所必须实现的善就越小,因为它被认为是可允许的。如果故意杀害无辜的战斗人员并不是一个人可以做的最糟糕的杀戮,那么必须实现的善就会比例如故意杀害无辜平民的情况要少,因为哲学家们倾向于认为只有在最高的紧急情况下才可以允许故意杀害无辜平民。这可能意味着,即使在普通的战争情况下,故意杀害无辜士兵也是可以允许的。
那么,战争可以通过可杀性和较小的邪恶理由相结合的方式来证明其合理性。一些不正义的战斗人员失去了不被杀害的权利。其他人的权利可以被剥夺,但这并不意味着不正义的非战斗人员的权利也可以被推翻。我们可以拒绝责任困境中的和平主义号角。但温和的“战斗人员平等”很可能是真实的:因为杀害无辜的战斗人员并不是最糟糕的一种杀戮,所以不正义的战斗员相应地更容易为使用致命武力辩护(至少是对正义的战斗人员)。这就增加了他们能够满足区别原则、合比例性和必要性的情况范围,因此,战争是可以允许的。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道德区分的论证。一些论证集中在为什么杀害无辜的非战斗人员是特别错误的;另一些论点集中在为什么杀害无辜的战斗人员并不那么糟糕。本节考虑的是第二种论证,在下一节再讨论第一种论证。 上面提到的修正主义者的论点也许不能作为可杀性的依据,但也许能证明宁愿伤害战斗人员的一些理由。战斗人员比非战斗人员能更好地避免伤害。与非战斗人员相比,战斗人员为避免其战友的错误行为而承担的责任肯定更大。而大多数战斗人员准备战斗——不管他们的事业是否正义——可能意味着,即使是正义的战斗人员相对于非战斗人员的地位也有些模糊不清。他们只是意外地符合对手的权利。与非战斗人员相比,他们在被错误杀害时的相抗理由更弱,因为非战斗人员更坚定地尊重他人的权利(关于坚定性和尊重,见Pettit 2015)。 此外,当战斗人员杀害其他战斗人员时,他们通常认为他们这样做是被允许的。他们通常认为,他们的理由是正当的,这是实现正当理由的合法手段。但是,只要他们是合法的战斗人员,他们也会相信国际法制约着他们的行动,因此,按照国际法作战,他们的行为就是被允许的。Lazar(2015c)认为,当你知道这样做在客观上是错误的时候杀人,比你合理地认为你的行为是允许的时候杀人,更令人反感。 基于同意的“战斗人员平等”的论证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的经验性而不是规范性的前提。如果战斗人员事实上放弃了不被对手杀害的权利,即使是在打正义战争的时候,那么这显然会影响对手的行动理由,减少了杀害任何放弃这一权利的人的不法性。问题是,他们并没有放弃不被杀害的权利。然而,他们往往确实提供了一个更有限的默示放弃权利的机会。拥有武装部队的目的,以及许多在其中服役的人的意图,是保护平民免受战争的掠夺。这意味着既要反击对他们的威胁,又要吸引他们的火力。战斗人员在敌人和他们的平民同胞之间横亘,并代表他们的同胞作战。如果他们遵守战争法,他们会明确地将自己与平民区分开来,穿上制服,公开携带武器。他们含蓄地对他们的对手说 "你应该放下你的武器。但如果你们要打,那就和我们打"。这构成了他们对不被伤害权利的有限放弃。像完全放弃一样,它改变了他们的对手所面临的理由——在这些情况下,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杀死非战斗人员会更糟糕。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非正义的战斗人员应该简单地停止战斗。但这种对对手权利的有条件放弃意味着,如果他们不打算放下武器,他们把战斗人员作为目标会比非战斗人员更好。 当然,人们可能会认为,凭借其利他主义的自我牺牲精神,正义的战斗人员实际上是最不应该受到战争伤害的(Tadros 2014)。但是,首先,战争并不是确保人们得到应有回报的一种手段。更重要的是,鉴于他们的利他主义是专门为了把火力从他们的非战斗同胞身上引开,如果把这当作做他们试图防止的事情的理由,那是有悖常理的。 这些论证和其他论证表明,杀害无辜的战斗人员并不是人们可以做的最坏的一种杀戮。因此,在战争的一般情况下,只要由此获得足够的好处,一切都可以被认为是允许的。如果非正义的战斗人员只攻击正义的战斗人员,并且如果他们通过这样做实现了一些有价值的目标——保护他们的战友、他们的同胞或他们的领土——那么他们的战争就可能是可允许的,即使他们侵犯了正义战斗人员的权利(Kamm 2004; Hurka2005; Kamm 2005; Steinhoff 2008; Lazar 2013)。至少,与我们把每个正义战斗人员的死亡视为等同于最严重的谋杀相比,他们可以合法地战斗是更有说服力的。这并不是在为“战斗人员平等”辩护——它只是表明,不公正的战斗人员比人们想象的更经常地可以进行合法的战斗。再加上所有的战争在道德上都是异质的,涉及正义和非正义的形态(Bazargan 2013),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即使战争法中的“战斗人员平等”缺乏基本的道德基础,它也是对真相的合理估计。 然而,一些哲学家试图为 "战斗人员平等"进行更有力的辩护。最突出的三条路线是制度主义的。契约论者(Benbaji,2008,2011)首先指出,国家(及其人民)需要有纪律的军队来进行国防建设。如果士兵总是要自己决定一场特定的战争是否公正,那么许多国家在需要的时候就无法组建军队。他们将无法阻止侵略。所有的国家和所有的人都受益于这样一种安排,即个别战斗人员放弃他们不被对方杀害的权利——服从国家的命令而不对每一次部署进行猜测。战斗人员默许以这种方式放弃自己的权利,因为他们都知道按照战争法作战涉及到这种放弃。此外,他们的同意是 "道德上有效的",因为它与国家间的公平和最佳契约相一致。 国际法似乎确实改变了战斗人员的道德地位。如果你加入一个国家的武装部队,你知道在国际法上,你因此成为武装冲突中的一个合法目标。这必须与伤害你的不法性有关,即使你是为正义事业而战。但Benbaji的论点比这更雄心勃勃。他认为,士兵们放弃了他们不被对方杀害的权利——不是上述有限的、有条件的放弃,而是彻底的放弃,这就免除了他们的对手的任何不法行为(尽管它并没有如此免除他们的军事和政治领导人)。 这个建议的第一个问题是,它依赖于有争议的经验推测,即士兵事实上是否以这种方式同意。但抛开这一点不谈,第二,它是彻底的国家主义,暗示国际法根本不适用于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之间的不对称冲突,因为后者不涉及适当的公约。这使得国际法的基础很浅薄,无法支持违反国际法的行为通常会引起的强烈的义愤。它还表明,那些不批准国际法主要条款的国家,或者退出协议的国家,可以逃脱国际法的约束。这似乎是错误的。第三,我们通常认为,当新的情况出现时,对基本权利的放弃是可以逆转的。为什么不允许正义的战斗人员在进行正义的战争时撤回对权利的放弃?许多人认为生命权是不可剥夺的;即使我们否认这一点,我们肯定会怀疑在信息不充分的条件下,你是否可以一次性让渡所有的生命权。此外,假设你想加入武装部队只是为了打一场特定的正义战争( McMahan 2011b)。既然你只打算现在打仗,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放弃你的不被伤害的权利?第四,也是最严重的一点,即使Benbaji的论证解释了为什么在战争中杀害战斗人员是被允许的,无论被杀的战斗人员追求的是什么事业,它也不能解释为什么非故意地杀害非战斗人员这一自己行动的附带效应是被允许的。通过加入他们国家的武装部队,士兵们至少做了一些事情,这意味着他们同意构建其角色的国际法制度。但非战斗人员并不同意这一制度。为不正义事业而战的士兵将不可避免地杀害许多无辜平民。如果这些死亡不能合比例,那么“战斗人员平等”就不成立。 第二种制度主义论点的出发点是这样的一个信念,即我们有义务遵守我们合法国家的法律。这使得被命令去打一场不正义的战争的不正义的战斗人员有理由去服从这些命令。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证明这一点。Estlund(2007)认为,服从命令的义务来自于国家的认识论权威——它比单个士兵更有可能知道这场战争是否正义(批评意见见Renzo 2013);Cheyney Ryan(2011)强调国家权威的民主来源,以及维持平民对军队控制的至关重要性。这些都是真正的道德理由,应该在士兵的考量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它们真的有足够的分量来支撑“战斗人员平等”吗?这一点似乎值得怀疑。它们不能系统地推翻非正义战斗员不杀害无辜者的义务。无论这些理由是否在平衡中占了分量,或者是阻碍其他理由被考虑的排他性理由,这一点都是成立的(Raz 1985)。无辜者不被杀害的权利是最重要的、最基本的权利。要想让其他理由超过它们,或将它们排除出考虑范围,必须是非常强大的理由。战斗人员服从命令的义务根本不够分量——正如每个人在服从非法的战时命令方面所认识到的那样(McMahan 2009: 66ff)。 与第一个论证一样,第三个制度主义论证也是以“战斗人员平等”的长期结果为基础。但它并不关注国家的自卫能力,而是强调限制战争恐怖的重要性,因为我们知道人们会在其事业的正义性上欺骗自己(Shue 2008,2010;Dill和Shue 2012;Shue 2013;Waldron 2016)。由于战斗人员和他们的领导人几乎总是认为自己是正确的,任何关于不正义的战斗人员放下武器的禁令都会被忽视,而任何伤害非战斗人员的额外许可都会被双方滥用。在几乎所有的战争中,只针对战斗人员就足以取得军事胜利。如果这样做能在长期内最大限度地减少非正常死亡,我们就应该责令所有各方,无论其目的如何,都要尊重“区分”。此外,虽然甚至在什么是战争的正当理由方面也很难取得国际共识(见证了关于侵略罪的罗马法规的争议,经过多年的谈判,外交官们才达成了一个不容易的妥协),但战时正义(jus in bello)的传统主义原则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国际支持。它们是来之不易的让步,只有当我们确信新的制度将是一种改进时,我们才应该放弃这些原则(Roberts 2008)。 虽然这个论证是有道理的,但它并没有解决与之前的以行为为重点的论证相同的问题。我们可以问的一件事是:在特定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做?在阿富汗,或马里,或叙利亚,或索马里,士兵应该如何行动?当我们问这个问题时,我们不应该一开始就假设我们或他们显然不能遵守我们可能提出的任何严格的道德标准(Lazar 2012a;Lazar and Valentini forthcoming)。在考虑我们自己的行为以及我们对其有影响力的人的行为时,我们应该从所有可用的选项中进行选择,而不是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太不道德而将一些选项排除在外。另一方面,在设计制度和法律时,我们当然应该考虑人们可能会如何回应它们。我们需要回答这两类问题:我真正应该做什么?考虑到我和其他人的可预见的脆弱性,法律应该是什么? 那么,温和的“战斗人员平等”是避免责任困境中和平主义号角的可能结果。为了证明战争中的杀戮是可允许的,我们需要证明,故意杀害无辜的战斗人员并不像故意杀害无辜的非战斗人员那样是一个严重错误。而且,如果杀害无辜的战斗人员并不是最糟糕的一种杀戮,那么在最高紧急状态之外的普通战争中取得的利益就可以更合理地证明它是合理的。根据这一观点,与Walzer和他的批评者的观点相反,在正义战争中,许多有意的杀戮是可允许的,不是因为目标具有可杀性,而是因为侵犯他们的权利是一个可允许的较小的恶。但无论你是站在正义还是非正义的一方,这一原则都适用。这反过来又增加了站在非正义一方的战斗人员能够以可允许的方式进行战斗的范围:他们不需要为了证明侵犯正义战斗人员的权利而实现某种与避免最高紧急状态相当的利益,而只需要实现更加普通的利益,因为这些不是最糟糕的权利侵犯类型。因此,非正义的战斗人员保护彼此和同胞的相关责任,他们服从合法政府的责任,以及其他此类考虑,有时会使故意杀害正义战斗人员成为可允许的较小的罪恶,而使得非故意杀害非战斗人员成为合比例的。这意味着,现有的战争法比许多修正主义者认为的更接近战斗人员的真正道德义务。尽管如此,非正义战斗人员在战争中的许多杀戮行为在客观上仍然是错误的。  保护平民
保护平民正义战争理论中的中间道路取决于能否表明杀害平民比杀害士兵更糟糕。本节讨论了解释为什么杀害平民是明显令人反感的论证。我们将在下文中讨论,在考虑合比例性时,故意杀人的重要性。 这些论点在Lazar (2015c)中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在此仅作简要介绍。它们建立在一个关键点上:“道德区分”说的是,杀害平民比杀害士兵更糟糕。它并没有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杀害平民比杀害士兵更糟糕。Lazar持有这一更强的原则,但不认为杀害平民和杀害士兵之间的内在差异——在这两种杀戮中必然体现的属性——有足够的分量为“道德区分”提供在战争中保护非战斗人员所需的那种规范力量。这种保护取决于调动道德区分的多种基础,其中包括许多属性,这些属性在杀害平民和杀害士兵的行为中被偶然地但持续地体现,从而使杀害平民的行为变得更糟。我们不能把道德区别单独建立在这些属性中的任何一个,因为每个属性都容易受到反例的反对。但是,如果把它们放在一起,它们就能证明伤害非战斗人员和伤害战斗人员之间有一条相对明确的界限。当然,也有一些困难的案例,但这些案例必须以突出的基本属性来决定,而不是仅仅以属于一个或另一个群体的事实为依据。 首先,至少在战争中故意杀害平民,即使是在必要性限制的最宽松的解释中,通常也是不成立的。这并不总是正确的——如果杀戮能有效地实现你的目标,并且没有其他有效的选择,那么杀戮就是必要的。杀害平民有时符合这一描述。这一论断往往是有效的:对德国的封锁有助于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尽管它可能造成多达50万平民死亡;俄罗斯在车臣以平民为目标的攻击减少了俄罗斯战斗人员的伤亡(Lyall 2009);塔利班的反平民战术在阿富汗是有效的。而这些攻击往往是战争中的团体最后的手段(Valentino 2004);当所有其他选择都失败或成本过高时,以平民为目标是相对容易做到的。事实上,正如最近的恐怖袭击所显示的那样(例如,孟买和巴黎),少于10个蓄意的枪手用基本的武器就可以使世界上最活跃的城市停摆。因此,杀害平民可以满足必要性的限制。尽管如此,对平民的攻击往往是完全过分的,而且在过分地或为其本身而杀害无辜的人时有一种特别的蔑视。至少,如果你有一些战略目标在望,你可能会认为有些东西的重要性超过了被杀害的无辜生命。那些毫无意义地杀害平民的人在这样做的时候表达了他们对受害者的完全漠视。 第二,即使杀害平民是有效的,也通常是出于机会主义(opportunistically)(Quinn 1989;Frowe 2008;Quong 2009;Tadros 2011)。也就是说,平民的痛苦被用来作为迫使他们的同胞和领导人结束战争的手段。对平民中心的围困和空袭是为了摧毁民众和政府的意志。相比之下,战斗人员几乎总是被消灭性地杀害——他们的死亡不是为了获得不以这种方式使用他们就无法获得的利益;相反,他们被杀害是为了解决他们自己造成的问题。这似乎也与这些类型的攻击的相对不法性有关。当然,在战略层面上,每一次死亡都是为了向敌人的领导层传达一个信息,即继续战斗的成本大于收益。但在战术层面,也就是实际杀戮发生的地方,士兵们通常是消消灭地杀死士兵,而他们则是机会性地杀死平民。如果这种差异在道德上是重要的,就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如果杀害平民的行为比杀害士兵的行为更经常是机会主义的,那么杀害平民的行为一般来说就比杀害士兵的行为更糟糕。这就进一步支持了“道德区分”的观点。 第三,如上所述,行动者的信念可以影响她的杀人行为的客观严重性。当你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杀人在客观上是被允许的时候,与你伤害他们的认识论基础较弱的时候相比,杀人对这个人的伤害就不那么严重。更确切地说,杀一个无辜的人,凶手越有理由相信没有可杀性,那么对她的杀害就越是严重的错误(Lazar 2015a)。
最后,在关于战争道德的普通思考中,最常被引用来解释伤害平民的独特的不法性的两个属性,在他们的无辜之后,是他们的脆弱性和他们的无防卫性。Lazar(2015c)怀疑,保护脆弱者和不伤害无防卫能力者的义务几乎与不伤害无辜者的义务一样基本。(注意,这些义务只适用于其对象在道德上是无辜的。)显然,在任何合理的分析中,平民比士兵更脆弱,更无防卫能力,所以如果杀害更脆弱和无防卫能力的无辜者更糟糕,那么杀害平民就比杀害士兵更糟糕。 毫无疑问,士兵也常常是脆弱的——人们想到了1991年伊拉克的 "死亡公路",当时美军摧毁了伊拉克军队的多个装甲师,这些装甲师完全没有保护措施(这些师中的许多人员逃进了沙漠)。但这个例子只是表明,在士兵处于弱势和无防备的情况下,杀死此时的他们比杀死并非无防备的他们更难以正当化。如果士兵比平民更脆弱和无防卫能力的经验说法是真的,那么这只是支持了“道德区分”的例子。  合比例性
合比例性 坚持道德区分原则可以使人摆脱责任困境中的现实主义和和平主义号角,同时还能赋予责任以应有的地位。即使是否认温和的战斗人员平等的修正主义者也可以赞同道德上的区别,从而保留非常合理的见解,即杀害正义非战斗人员比杀害正义战斗人员更糟糕。而且,如果他们要解释大多数人对战争的深思熟虑的判断,即使是和平主义者也需要对为什么杀害平民比杀害士兵更糟糕做出一些解释。 然而,“道德区分”不是“区别原则”(Discrimination)。它是一种比较性的主张,而且它并不涉及意图。相比之下,区别原则禁止故意攻击非战斗人员,除非在极度紧急的情况下才会允许。它与 "合比例性"相对应,对非故意杀害非战斗人员的限制要弱得多。只有在可怕的危机中,才可以允许故意攻击非战斗人员。但在个别战斗中取得的普通成果可以证明非故意的杀戮是合理的。是什么证立了这种过度的区别? 这是规范伦理学中最古老的问题之一(不过最近的辩论,见Quinn 1989;Rickless 1997;McIntyre 2001;Delaney 2006;Thomson 2008;Tadros 2015)。在大多数情况下,那些有意伤害受害者的人比那些附带地、不可避免地伤害他们的人,表现出更令人讨厌的不尊重。也许对意图的意义最好的论证是,首先,在一般的论证中,心理状态与客观可允许性有关(Christopher 1998;也见Tadros 2011)。其次,我们需要一个丰富而统一的理论解释,说明以这种方式重要的具体心理状态,而意图则适合于此。也许,特别禁止故意攻击平民的做法是一种对道德真相的夸张。意图确实很重要。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故意杀人比非故意杀人更糟糕(尽管一些完全疏忽或对受害者漠不关心的非故意杀人几乎和故意杀人一样糟糕)。但它们之间的区别并不是绝对的。它不能维持一方面是近乎绝对的禁止,另一方面是全面的允许,这两者之间的截然不同。
当然,这正是那种细微的差别,如果在国际法中实施,或者被战斗人员认为是一种规范,将是灾难性的。在战争中权衡生命,对信息的要求非常高。士兵们需要一个他们可以应用的原则。区别原则就是这个原则。它不仅仅是一个经验法则,因为它涉及到一些有道德基础的东西——杀死平民比杀死士兵更糟糕。但它也是一个经验法则,因为它在有意和无意的杀戮之间划出了一个比内在的道德合理更鲜明的对比。 首先,国际法中的合比例性与一阶道德理论支持的原则版本有明显的不同。在法律上,只要对平民的伤害与由此实现的具体和直接的军事利益相比并非相差甚远,战争行为就是合比例的。如上所述,从一阶道德的角度来看,这是无法理解的。但是,对于这种中立的合比例性概念,可能有一个更好的制度性论证。合比例性的计算涉及许多实质性的价值判断——例如,关于道德地位、意图、风险、脆弱性、无防卫能力等的意义。这些都是非常有争议的话题。合理的分歧比比皆是。许多自由主义者认为,胁迫性法律应该以其他人能够合理接受的条款来证明,而不是取决于一个人的总体道德理论中的有争议的内容(Rawls 1996: 217)。武装冲突法是强制性的;违反则构成战争罪,可以受到惩罚。当然,一个更复杂的法律是不可运作的,但我们也有原则性的理由不把国际法建立在当代的有争议的正义战争理论上。也许目前的标准可以从更广泛的总体道德理论中得到认可,而不是从任何其他更接近于事实的东西中得到认可。 第二,抛开法律,再次关注道德,许多人认为责任对于思考合比例性至关重要,具体如下。假设叙利亚自由军(FSA)对伊斯兰国的大本营拉卡发起攻击。他们预测在进攻中会造成一些平民伤亡,但这只是因为伊斯兰国选择在平民区行动,迫使平民成为 "非自愿的人盾"。一些人认为,伊斯兰国对将这些平民置于危险之中负有责任,这使得自由军在决策时对这些平民的生命重视程度低于伊斯兰国没有将他们作为人盾的情况下(Walzer 2009;Keinon 2014)。 但人们也可以考虑以下问题:即使伊斯兰国在利用平民作掩护方面有很大的过错,但为什么这就意味着这些平民在受到伤害时享受的保护更弱?我们通常认为,一个人只应该通过自身的行为失去或丧失自己的权利。但根据这一论证,平民享有较弱的保护,却不是因为他们自己的过错或选择。有些人可能认为,对非自愿的人肉盾牌适用更宽松的标准,因为它具有阻止人们以这种方式利用道德的额外价值(Smilansky 2010;Keinon 2014)。但这个论点似乎是奇怪的循环:我们通过摒弃道德克制来惩罚人们对我们的道德克制的利用。更重要的是,这种行为从可以预见的杀害平民作为反击军事威胁的不可避免的附带效应,变成了杀害这些平民作为阻止未来攻击的手段。这使他们成为一种工具,使伤害他们的行为更难以自圆其说。 
必要性 上述考虑也都与必要性有关。它们使我们能够权衡利害关系,以便我们能够确定是否能够以代理人的合理成本来减少所造成的道德上的伤害。必要性的基本结构在战前正义(jus ad bellum)和战时正义(jus in bello)都是一样的,但显然在实质上会出现与合比例性相同的差异。有些理由只适用于战时正义(jus in bello)的必要性判断,而不适用于战前正义(jus ad bellum)的判断,因为它们是以整个战争将继续的背景假设为条件的。这意味着,我们不能通过简单地加总我们对共同构成战争的个别行动的判断来得出对整个战争的必要性的判断。 例如,在应用必要性原则时,战时正义(jus in bello)的核心问题之一是:为了尽量减少对无辜者的伤害,我们需要使自己的部队承担多大的风险?有些选择可能仅仅是为了拯救我们一些战斗人员的生命而有必要。在战前正义(jus ad bellum)中,从整场战争的角度来看,我们当然要考虑我们自己的战斗人员所面临的风险。但我们是以不同的方式来考虑的——我们要问的是,整个战争所取得的成果是否能证明让我们的战斗人员处于危险之中是合理的。这样,我们就不会把在战争中采取的多种行动将拯救个别战斗人员的生命这一事实算作战争所取得的成果。我们不能把避免只有在我们决定开战的情况下才会出现的威胁算在证明开战决定的好处中。 这直接关系到国际法中经常被忽视的要求,即战斗人员必须 "在选择攻击手段和方法时采取一切可行的预防措施,以避免并在任何情况下尽量减少平民生命的附带损失、对平民的伤害和对民用物体的损害。(《日内瓦公约》第57条第2(a)(ii)款)" 这有很深厚的道德基础:战争中的战斗人员在道德上被要求减少对无辜者的风险,直到进一步这样做会给他们带来不合理的高成本使他们不堪重负。要想知道何时达到这一点,就需要思考:士兵承担风险的角色义务;对平民造成伤害与允许伤害发生在自己或战友身上的区别;保护战友的相关义务的重要性;以及已经提出的支持“道德区分”的所有考虑。这种计算是很难进行的。我自己的观点是,战斗人员应该优先考虑平民的生命(Walzer andMargalit 2009; McMahan 2010b)。这与现有的实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Luban 2014)。 
 正义战争理论的前景
正义战争理论的前景 最近的许多工作都使用了传统主义或修正主义的正义战争理论来考虑战争实践中的新发展,特别是无人机的使用,以及自动武器系统的可能发展。其他人则专注于非国家冲突和不对称战争的伦理问题。很少有当代战争符合二十世纪中期的民族国家模式,而涉及非国家行为者的冲突对合法权力,特别是区别原则提出了有趣的问题(Parry 2016)。由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可怕失败所引发的第三个发展是对战争后果的反思浪潮。这个话题,即战后正义( jus post bellum),将单独讨论。 至于正义战争理论的哲学基础:传统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立场现在已经明确了。但是,在处理那些有待回答的真正有趣的问题时,不应考虑到这种分裂。最值得注意的是,政治哲学家可能对正义战争理论的辩论有更多贡献。同样有趣的是,以更开放的心态来思考国际法制度(例如,还没有人证明武装冲突法具有权威性的说法),以及民族国家内部军队在非战时的作用(Ryan 2016)。 战争的集体层面可以得到更充分的探讨。一些哲学家已经考虑了士兵在战斗时如何 "共同行动"(Zohar 1993;Kutz 2005;Bazargan 2013)。但很少有人反思群体在战争中是否存在并具有道德意义。而从表面上看,用这些术语来讨论战争是非常自然的,尤其是在评价整个战争的时候。当英国议会在2015年底辩论是否加入对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伊斯兰国的战争时,无疑每个议员也在思考她应该怎么做。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在问自己英国应该怎么做。这种团体行动可能完全可以还原为组成其的个人行动。但这仍然提出了有趣的问题:特别是,作为代表群体行动的个人,我应该如何为自己的行动辩护?我必须只诉诸于适用于我的理由吗?或者我可以根据适用于团体其他成员或整个团体的理由行事?我是否可以只评估我的行动的可允许性,而不去评估自己行为作为其中一部分的团体行动?尽管集体主义思想在战争中非常突出,但对战争的群体道德的讨论还处于起步阶段。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Philosophia 哲学社
推荐阅读:
版权声明:“备战深国交网”除发布相关深国交原创文章内容外,致力于分享国际生优秀学习干货文章。如涉及版权问题,敬请原作者原谅,并联系微信547840900(备战深国交)进行处理。另外,备考深国交,了解深国交及计划参与深国交项目合作均可添加QQ/微信:547840900(加好友时请标明身份否则极有可能加不上),转载请保留出处和链接!
非常欢迎品牌的推广以及战略合作,请将您的合作方案发邮件至v@scieok.cn本文链接:http://cambridge.scieok.cn/post/2900.html
-
- “女权文书”成Top 20“金钥匙”?你连伪女权都辨认不出,别做梦了!
- 精神分析为何认为性的二分不具有任何意义? / 翻译
- 什么是政治性抑郁 -- 其符合美国心理学会(APA)的抑郁症标准
- 柯尔施:《资本论》导论 / 翻译
什么是战争中的正义:正义战争理论 (下)
25374 人参与 2022年03月16日 14:20 分类 : 深国交哲学社 评论
search zhannei
深国交2024年英美本科录取小计
-

未标注”原创“的文章均转载自于网络上公开信息,原创不易,转载请标明出处
深国交备考 |
如何备考深国交 |
深国交考试 |
深国交培训机构 |
备战深国交 |
联系方式
Copyright www.ScieOk.cn Some Rights Reserved.网站备案号:京ICP备19023092号-1商务合作
友情链接:X-Rights.org |中国校园反性骚扰组织 | 留学百词斩 | 南非好望角芦荟胶 | 云南教师招聘考试网 | 备战韦尔斯利网| 备战Wellesl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