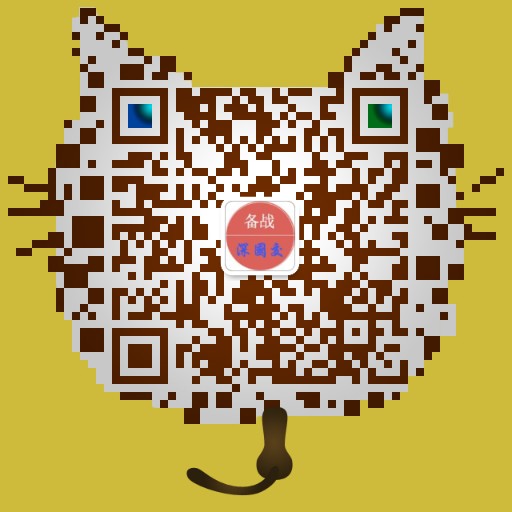当前位置:首页 » 深国交哲学社 » 正文
-

朱迪思·雷沃尔 (Judith Revel),法国哲学家和翻译家。 一部文集的地位总是很难勘定。是否在其中势必要回溯地确认一种思想的一致性、一项研究在某一给定时刻的主题上的统一性,以及对一个时代的见证?亦或是否要反之强调所涉及的主题和论战的角度、合作与影响、移位与重组之广泛?最后,是否要将它当作自身封闭的对象:如同一本书那令人安心的事无巨细暂且悬置了我们的疑惑,而文集所汇聚的问题和开端 (ouvertures) 却反而有时深触我们的现在? 读者在这文集中将会遭遇的文章,无疑配得上所有的这些特征,但也配得上其他的存在。这些写就于90年代初到00年代末的文章,涵盖了奈格里在其远不止十五年的研究和斗争的共同体经验中的工作,并且抛开其期刊 (revue) 的形式(Futur Antérieur 然后是 Multitudes)则是根本无法理解的。这些期刊就自身而言已是政治的项目,因为它们总要在理论分析和对现实的反应之间,在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或者社会学和福柯在其生命的尽头所言的「新闻学」 (实则是对一种深植于我们的现在的新批判态度的称谓) 之间找到恰当的距离——或者说是学科之间来来往往的节奏。从这个角度来说,期刊是最灵活也最有效的介入形式;而文章以及社论,有时甚至是由我们四个人联手写成,则同时表明了分析的进展和岁月的变迁。 然而,这十五年绝非某一无足轻重的阶段。如果采取一种严格的奈格里传记的角度,这十五年意味着他流亡法国的最后时光,回归意大利及随之而来的六年监禁,还有最后的重见自由。这也是与迈克尔·哈特合作的三部著作:《帝国》,甫一问世便取得全球赞誉;然后是《诸众》,再加上最近的《大同世界》得到写作与出版的时光。 然而这些时光同样以其自己的方式,成为了从埃里希·霍布斯鲍姆曾如此准确定义过的「短20世纪」的最终出走:从柏林墙的倒塌到苏联的解体,紧接着就是Futur Antérieur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时的创刊。因此,我们所面临的也就不仅仅是20世纪的结束、21世纪的开始,还是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的转折点,从一种语法到另一种的转折点,同样,也很可能是从一套分析工具到另一套的转折点。 当然,我们也可列举出一些事件:在过渡时期的转折点,这些事件为了从此种政治现代性——我们本以为它会永远年轻——的出走各自作出了贡献。散漫地列举如下:两次海湾战争,法国的1995年总罢工,以及更广泛的、前所未见的斗争形式(随之而来的是新的政治主体性),意大利的贝卢斯科尼主义的诞生,郊区 (des banlieues) 的问题的涌现,另类全球化 (altermondialiste) 运动的开始,欧洲一体化建设的必要(及僵局),教会的政治角色,向认知资本主义 (capitalisme cognitif) 的过渡等等。现在,汇编这些文章自有其重要性;以及当然,如果说这册汇编只包含奈格里对某一给定时代的有限的作品选,那么也要指出,在此所展现的已经足以使读者看到其关键:一个真正的、关乎政治调查与分析的实验室。思想便如此成形:在思辨得到生产和组装之处、在新的概念得到试验之处、在新的假说冒险之处。 
奈格里于1969年创办了工人力量组织 (Potere Operaio) 而且成为著名的「自治运动」 (Autonomia Operaia) 的领军人物。这是这个运动的照片。
目的当然不在于回溯地指出,在那个时代谁有先见之明而谁又没有,谁成功地预见了时代,或者谁有那么一瞬无谓地尝试沿着死路走下去。 更值得关注的反而似乎是从中可辨识出的四大主题群,它们也在一定程度上昭示了与这些文本同时写就的著作。我们可以以图式的方式将这些主题定义如下: ——从对于国家形式的批判(如同奈格里在70年代和80年前后所表达的)过渡到对于一个新的形象:帝国的分析。这一分析重估了往昔对民族国家 (l' État-Nation) 的批判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以便分析当下。民族国家的主权,实质是藉由四个大一统原则为现代政治思想所定义的(领土的大一统,语言和文化的大一统,货币的大一统,军事的大一统),而今天的全球化对此提出质疑:全球化的权力,在一个有着不同的节段性的空间当中,以另一种方式组织起来(毕竟,边界根据经济的局势时开时闭,而后者的法律则关注于对人口流动的管理);就其文化和语言来看,它在很大程度上已然同质化;它并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而毋宁说是在律师和金融事务所里、在巨型的国际商务机构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者世界银行里,而不是在各国各部长的办公室里建立起来的。在这种语境下,战争自己也失去了其现代特征(对主权和领土的防御)而变成了其他的事件:预防性的、人道主义的、远距离的、在其领土边界之外的等等。控制的各种运作模式不断延伸和增长,并且有时使得高强度的治安行动和低强度的军事行动几乎不可区分。最后,基准货币(对于贸易而言)的弊端也已经显露: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打开了今天全球范围内为贸易货币霸权的竞争,而陈旧的「铸币权」业已被淘汰。 
——对于新的政治主体性,新的组织、行动和斗争的模态的确认。从对具体事件(1995年的罢工、西雅图的另类全球化运动到2001年八国集团在热那亚的峰会,以及郊区等等)的分析开始,对于奈格里而言,所要回答的根本问题在于:在《帝国》所翻开的新篇章中,可以存在怎样的与之对抗的政治主体性?奈格里的有时是极为具体的工作,常常为我们揭示这一主体性的哲学根基:通过重拾斯宾诺莎的诸众的概念,那将要来临的实则是一种前所未见的、关于不可化约的差异(这也就是说奇异性/singularité)的联结。一种关于「仅仅是作为差异的差异」的装配,其潜能恰只在于差异对大一统的拒斥;以及,以总是全新的方式,根据力的关系 (des rapports de force) 而在永恒的变化中创造诸种主体形态。然而,在重申斯宾诺莎的哲学(譬如诸众的概念)之外,也必须注意到其中的福柯的主体性生产(毕竟,应该将自我的创造当做是一种伦理的和政治的实践,哪怕是身处最密不透风的权力网络之中)以及德勒兹的生成(对抗一种「同一身份」/identité的政治)的主题:总而言之,这意味着,现代性曾使得我们习于以如此这般的陈旧范式来思考政治主体,如今它们再一次显得过时,而我们亦必须创造出新的主体性以匹配我们的现实。 ——对于经济生产的范式(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作的范式)突变特征的分析。对于向我们今天所说的认知资本主义(这也就是说向一种认识/connaissance、情感/affects与合作/coopération的经济)过渡的描述,在奈格里的分析之中,是紧接着他在70年代对这第一种突变(即从「大众-工人」/ouvrier-masse 向「社会-工人」/ouvrier-social 的过渡)的表达的。实际上,这也就是要使得福特制的工作机构的趋于解体、以及更为复杂的组织的生成更清晰可见,后者将工人的主体性(「社会性」)一定程度上地整合进来,而不再仅仅是其物理的、非主体性的劳动力——在这部文集的某些文本之中,有时也被奈格里称作是「后福特制工作」或者「非物质工作」。 
奈格里的分析所经历的演变便也十分明显了:对于不可抗的从福特制的出走(尽管只有零星的趋势)的简要确认,抑或是对工作的非物质性(不同于物质工作:藉由物理劳动力进行连续的商品再生产)的证实,直到一种基于认识和社会合作的经济的、真正的资本主义,这个想法超越了通常的物质/非物质的二元对立,并赋予这种对立一个更加积极的面向;这不得不说是一项将假说和验证联结起来的热情洋溢的工作。以及,一直以来某种「雅努斯的结构」的或曰双面性的分析:一方面,事实上是要描述在自1968年起的数十年的斗争之后,资本主义是如何一定程度上在工厂之外重新组织起来,并修正其奴役和剥削(这也就是说价值的生产)的布置 (dispositifs) 以便封锁和控制劳动力的主体性的;另一方面,这同一种对于资本主义价值生产已然不可或缺的主体性,如何在被更为严密控制着(盖它被封锁在生产活动之中)的同时亦悖谬地更为强大(盖它对于资本不可或缺)。总而言之:在生产过程与资本主义的增值之中新加入的主体性的生产与社会化的机制,既是资本主义的奴役和控制的延伸,也悖谬地就是一架被引入资本之中的特洛伊木马——因为如果主体性是斗争的引擎,那么认知的生产 (production cognitive) 离开了主体性就什么也不是。 我们也知晓米歇尔·福柯的分析:权力关系究竟如何变成了生命政治 (biopolitiques) ——这也就是说,当权力延伸到生命的方方面面之时——以迎合经济自由主义以及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诞生,以及使利润最大化成为可能。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从十九世纪初开始,治理工人的生命就意味着控制生命的所有样态,并使它完全为了生产而运转。在奈格里的理论中,重拾「生命政治」这个概念来刻画现实的增值过程,相反是意在描述生命的方方面面都投入到工作之中:生命不再是使得生产成为可能之物,而甚至是生产的原材料 (matière) ;它要被捕获、剥削、奴役,因为它「在其自身之中」(en elle-même) 就是有价值的。 然而,生命不仅仅是身体的生物学或者生理学面向——正如生命政治并非简单的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对生命的剥削。对生命政治的批判远要更加丰富,它总是不满于那些将bios还原为zoè的大祭司们——声称生命总是受限于它自己所谓自然性的信徒们。因为生命首先是关系、情感与合作的集合,知识 (savoir) 与语言、姿态与确认 (connaissance) 的回环,它们在日常生活中织起我们共有的并且总是基于劳作之上的社会性,而我们已然身处其中。生命是对主体性、对存在的样态、对行动与组织的模态的冗长而决绝的构建;正是这种创造和试验的充盈,在目前的一切限制的内部(当然不能否认这一点)有所革新。这便是奈格里有时所称的本体论(这也就是说要字面地理解,这是关于崭新的、绝对内在的存在形式的创造)。这样的生命——或者用其他的说法:这种本体论的生产——总是为资本所尝试着吸纳。于是,要如何尽可能地避免资本从使这种革新的生产成为可能的主体性中夺取它?要如何阻止资本将在定义上本就是属于所有人之物据为己有?以及,我们还得面对:如何反思今后将比物质商品的生产更值得注意的社会的生产及其相应的经济机器的运转?资本需要建立怎样的控制、增值以及衡量的系统,来适应于这种新的社会生产?并且,要以怎样的战略来反对与这些前所未见的形式相契合的、逐渐获得其界定的新经济图景? ——最后一个主题群即在前三个的相遇中诞生。共同性的主题潜藏在这部文集最后几个文本的脉络之中——同时又明现在最末尾的文本之中——既诞生在定义这些社会生产的新形式的必要之中、也诞生在指出私有/公有这一对子(现代的政治思想早已使我们习于这样思考)早已过时的迫切之中。 不过,共同性从来都没有代表过任何政治的或者是司法的挑战——对于罗马法而言,共同性应该被定义为是所有人都可拥有的——公有性或者私有性只是建立在人们在政治上已定义其对立者的地位之上,但是它们实际上都包含了财产的观念,这也就是说,几可认为私有化和公有化总是一种剥夺的行动。所谓「私有的」无非是仅为一人所有的(排除其他所有人的),而所谓「公有的」无非是国家所有的而并不属于所有人(因为它不属于任何一人)。因此,要超越公有/私有的范畴以设想共同性的哲学、法学和政治学的地位,就不得不首先包含一种对于财产和收益就它们自己而言的批判。 但是,从诸众的主体性构成的角度来看,共同性正是在奇异性之间的交往、合作与交换之中建立起来的:这并不是如我们长时间以来所认为的共同体的根源、基底或甚至是超验的原则,相反,它是诸众这个政治生产的另一个产物;或者更确切地说,如果「诸众」就是这个关于「仅仅是作为差异的差异」的充满潜能的装配之名,那么共同性就是诸众的革新的生产。共同性:这既是人们一同建立之物(而资本想要捕获并扭曲成私有和国有的双重形态),也是诸众的一个政治计划的名字。并且,「共同性」,这一新的政治空间的创造,后者足以对抗陈旧的普遍性的种种迂腐形象——现在,普遍性业已被还原到其空洞的拜物教形态,变得超验起来,摇身一变成为试图统一或者中和差异的粗鄙的面纱;总而言之,是以表面上的民主之名,使真正的民主成为神话。 最后,要明白共同性如何能够就其自身生成一种新的普遍性,不再是通过某一套原则来获取的、被置于所有事物的基础之上的普遍性,而是被建立起、被欲望着、被以绝对的民主的名义创造出、被根据着我们所栖身的时代的突变来反思的普遍性。它也首先是这样一种普遍性:关乎奇异性及它们之间的合作,关乎奇异性的自由的主体化实践,也关乎在社会的和政治的意义上体面地生活的权利。毫无疑问,批判性思想的实验室仍然向所有人敞开;而奈格里,正如他所拥有的充满潜力的奇异性,也绝不会停下为它作贡献的脚步。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2010年2月于巴黎 Judith Revel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Philosophia 哲学社
推荐阅读:
版权声明:“备战深国交网”除发布相关深国交原创文章内容外,致力于分享国际生优秀学习干货文章。如涉及版权问题,敬请原作者原谅,并联系微信547840900(备战深国交)进行处理。另外,备考深国交,了解深国交及计划参与深国交项目合作均可添加QQ/微信:547840900(加好友时请标明身份否则极有可能加不上),转载请保留出处和链接!
非常欢迎品牌的推广以及战略合作,请将您的合作方案发邮件至v@scieok.cn本文链接:http://cambridge.scieok.cn/post/4525.html
-
- 人文网站UnitedHumanitiesSocietyWebsiteUHsoc上线啦!
- 虚无现象学是否可能?卡尔纳普与海德格尔的争辩 (上)/ 翻译
- 偏见导致的不信任为何构成一种错待?
- 克利福德·格尔茨:反反相对主义 / 翻译
让思想成为共同性的实验室 / 翻译
34778 人参与 2024年02月04日 14:59 分类 : 深国交哲学社 评论
search zhannei
深国交2024年英美本科录取小计
-

未标注”原创“的文章均转载自于网络上公开信息,原创不易,转载请标明出处
深国交备考 |
如何备考深国交 |
深国交考试 |
深国交培训机构 |
备战深国交 |
联系方式
Copyright www.ScieOk.cn Some Rights Reserved.网站备案号:京ICP备19023092号-1商务合作
友情链接:X-Rights.org |中国校园反性骚扰组织 | 留学百词斩 | 南非好望角芦荟胶 | 云南教师招聘考试网 | 备战韦尔斯利网| 备战Wellesley